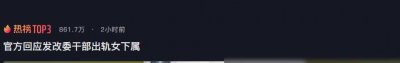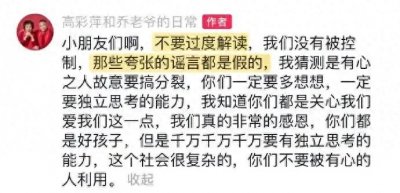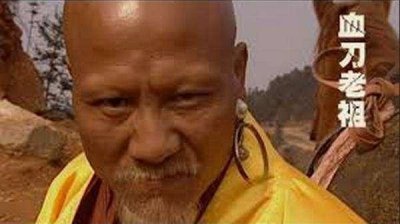村里的王寡妇和傻子好上了
村里的王寡妇和傻子好上了
村东头的老槐树被雷劈断那晚,王春娥正蹲在灶台前熬药。浓稠的苦味混着潮湿的霉气往鼻孔里钻,她拿火钳拨了拨柴火,火星子噼啪溅在青砖地上,像撒了把红亮的糖豆。
"春娥姐!春娥姐!"门板被拍得山响,雨水顺着门缝渗进来。王春娥撩起围裙擦手,刚开条缝,浑身湿透的李二狗就撞进来,蓑衣上滚着水珠子:"傻子掉沟里了!"
她抄起斗笠往外冲。雨帘子横着抽在脸上,村道成了条泥河,远处老槐树的枝桠在闪电里张牙舞爪。河沟边上聚着七八个人,油纸伞在风里打转。王春娥拨开人群,看见阿满大半个身子泡在浑水里,裤腿让荆棘勾破了,右腿弯成奇怪的角度。

"都杵着干啥?"她嗓子发紧。男人们互相瞅着,老赵头吧嗒旱烟:"这傻子三天两头惹祸......"
话音未落,王春娥已经蹚进沟里。黄泥水没到腰际,腐叶沾在衣襟上。阿满的脸比纸还白,嘴唇泛青,却冲她嘿嘿笑:"娥、娥姐......"三十岁的人,笑起来还像个孩子。
等把人背到卫生所,王春娥才发现自己光着脚。塑料凉鞋不知丢在哪里,脚底板被碎石子硌得渗血。赤脚医生老周推着眼镜看X光片:"胫骨骨折,得打石膏。"转身取药时嘀咕:"管这闲事,当心沾晦气。"
这话像根刺扎进肉里。王春娥攥紧湿漉漉的衣角,想起三年前男人咽气时,婆婆也是这样说的:"克夫相,命里带煞。"
诊室的白炽灯嗡嗡响,阿满躺在病床上啃苹果,汁水顺着下巴流。王春娥绞了热毛巾给他擦脸,瞥见他脖颈后那道月牙疤——听说是七岁那年发高烧,他爹用火钳烫的,说要把附身的邪祟赶出去。
"娥姐香。"阿满忽然凑近她衣领,鼻尖翕动。王春娥慌忙后退,撞翻了搪瓷盆。外间传来嗤笑,几个看热闹的妇女扒着门框,眼珠子滴溜溜转。
第二天晌午,王春娥挎着竹篮去送饭。刚拐过碾米房,就听见槐树下飘来闲话。

"说是救人,指不定......"张翠花的声音像沾了蜜的刀,"昨儿夜里我家那口子起夜,瞧见卫生所灯亮到鸡叫呢。"
"可不嘛,寡妇门前是非多。"刘婶子磕着瓜子,"要我说,傻子虽傻,到底是带把儿的......"
王春娥的指甲掐进掌心。竹篮里的鸡蛋汤晃出涟漪,映出自己发白的脸。她转身要走,却撞上个硬邦邦的胸膛。村支书赵有福捏着账本,目光在她胸口打了个转:"春娥啊,要注意影响。"
秋收前连着半个月放晴,晒谷场铺满金黄。阿满拄着拐杖在石磨旁转悠,王春娥教他剥玉米。粗粝的苞谷叶划拉手指,傻子学得认真,汗珠子挂在睫毛上。
"这不是挺能干么。"老周来换药时感叹。王春娥抿嘴笑,把晒好的决明子装进布袋——阿满夜里总说腿疼,得做个药枕。
变故来得比雨季还急。先是张翠花嚷嚷丢了银镯子,接着刘婶子家的腊肉少了两串。不知谁起的头,说瞧见阿满半夜在晒谷场转悠。赶集那天,傻子被堵在供销社门口,裤兜里掉出个亮闪闪的东西。
"我的镯子!"张翠花尖叫着扑上去。人群哗啦围成圈,不知谁踹了阿满一脚,石膏裂开条缝。王春娥挤进人堆时,正看见傻子蜷成虾米,怀里死死护着个蓝布包——是她给的芝麻糖,全压成了渣。

标签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