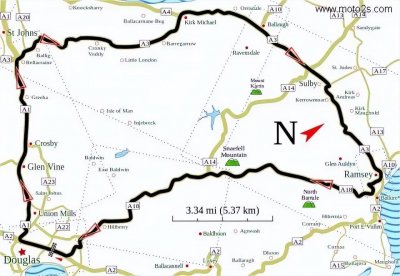乡村牛打架故事之一
乡村牛打架故事之一
小时候生活在乡下,有趣的事情极多,简直数都数不过来。
童年往事犹如雨后彩虹,忽闪在记忆的天空,即使云收雨散岁月老去,回想起来仍然鲜活闪亮,甚至比原来面貌更加吸睛夺目。
作为一个七岁起开始替父母分忧的放牛a崽,有趣的事情当然首推牛打架--可恨西风东渐,现在说的斗牛是西班牙的讲法,我们农村那时候只说牛打架--尤其水牛打架。那种登项(牛到壮年,颈项就会鼓起一大坨肉)水牛之间的斗殴,其激烈精彩惊心动魄之处,简直堪比战争大片,不,比大片还要让人销魂荡魄,多少年过去,至今还让村里的人津津乐道。
我们那地方三个寨子比邻而居,就是一座山下三面结寨,互成犄角之势,两条小河从远处绕寨而过,在不远处又汇聚合流,每个寨子前都面临小河。三百多年前,老祖宗相中这块风水宝地,拖家带口从湖南迤逦迁徙而来,让一姓子孙三处安营扎寨,相处甚是其乐融融,直到一场斗殴打破了昔日和谐,那就是牛打架。
我们寨是三个寨子中最大的,木房多,人口众,猪狗牛羊成群,男人们嗓门洪亮,女人们手脚溜麻,地势面南背北,门户依山傍水,满寨房屋从半山腰鳞次栉比延伸到田坝边,活像一个大汉扎手舞脚地靠在一张大躺椅上,颇有点王者气象。但这王者气象也只体现在寨上的人吹牛皮厉害,吹起来有气势有派头,说起大话来一个二个牛的不行,我们称这种人为屁眼大,或者大屁眼。但人的屁眼到底能有多大?再大能大到哪里去?总是吹嘘而已,从没人随便脱了下来给人看。不料有一次吵架却完美地解决了这个极限猜想。那是队上夜晚开大会的时候,全寨社员毕集,寨子中间的书哥和沛生哥意见相左闹了起来,书哥见他大话没边,就质问沛生哥你屁眼到底有多大,沛生哥扯着嗓子猛吼一声:“老子的屁眼有黄桶大!”黄桶者,装稻谷黄豆的木桶是也,一桶可装七八百斤。人有屁眼而大如黄桶,足见这话儿硬是大得没谱,却呛得书哥张口结舌无话可说,亏他还是当过民办老师的人,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,脱裤子是检验屁眼大小的有效路径,只须一脱就足以扭转颓势,化险为夷。可惜书哥急智不足而舞技有余,哑在当场没了招,楞了两楞,随即捞起沛生哥的胳膊,扯着他当场扭起了秧歌。好家伙,在几盏马灯汽灯的照射下,两个糙汉子一边扭屁股一边哈哈大笑,笑得旁人目瞪口呆,搞不懂闹的是哪一出。这笑声其实大有讲究,书哥的笑是掩饰尴尬,沛生哥的笑是张扬得意,两人心中都烧着一团怒火,恨不得在秧歌舞中把对方扭成一团灰烬。
如此大屁眼的寨子,这么多爱吹牛的人,当然得有吹牛的本钱。咱们寨啥都可以吹:论干活勤快、论当兵的人多、论年轻人长的帅、论娶的媳妇漂亮、论小孩读书聪明、论楞头青打架厉害......这些都能吹个三天六夜不重样,可就是真正的牛这玩意吹不起来。吹牛吹牛,正本清源你得有头厉害的牛,一头能打的牛都没有,吹到天上去的牛也只是头蜗牛,黄桶大的屁眼也只算根针眼。在那个年代,农村娱乐项目何其少,放牛打架才是王道。窝心啊,实在是满寨的黄牛、水牛没一头能拿得出手,放它们出去与别寨的牛打架,立着尾巴次次败北,屁股上带着横七竖八的血印子,回回铩羽而归,让我们寨的大人和放牛a崽相当没面子。每次看牛打架真的只是看,踊跃喝彩也只是作壁上观,没有自家牛参与的打架,如同中国足迷看世界杯决赛,管你怎样心潮澎湃,任他场上攻势如潮,哪怕在电视机前喊破嗓子,赛事结束终究遗恨难平,怎么也轮不到自己的队伍表演,实在是中国球迷吹牛皮的兔唇,黄桶底上老大的一个破洞。
--待续。原想一气写完,时间不允许,后面陆续发头条。

标签: